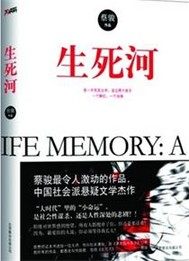漫畫–AQUARION COMPLETE–AQUARION COMPLETE
1995年6月19日,乙亥年壬午月辛巳日,農曆五月二十二,戌時,兇,“日時相沖,諸事失當”。
我死於亥。
歷年黑亮與霜凍,我城池去給姆媽上墳,屢屢城激化對身故的判辨。倘或死後還有人記得你,那就失效篤實逝,足足你還活在那些肉體上。即若躺在一座無主孤墳中,至少你還活在子孫的DNA裡。即令你連那麼點兒血統都沒留給,中低檔再有你的名字與肖像,留在出生證、教師證、戶口本、借書卡、拍浮卡、照相簿、卒業卷子……我多怕被大家記得啊!我叫闡發,曾是金朝東方學高三(2)班的櫃組長任。
我剛結果了一期人,隨後又被別樣人殛。
在使用廠房非法的魔女區,有把刀刺入我的脊。
戴着綴有紅布的粗紗,我篤信友好永遠睜體察睛,傳奇華廈何樂不爲,但我沒觀覽誅我的刺客的臉。
是否止住透氣?手腕有比不上脈搏?頸門靜脈還搏動嗎?血不復流動了嗎?氧愛莫能助消費中腦?末生腦壽終正寢?一絲一毫無權得和好留存。
發覺不到己方的消失,身爲死嗎?
衆人都說死的時候會很困苦,隨便被砍死吊死掐死悶死毒死溺死撞死摔死援例病死……下一場是窮盡的顧影自憐。
第二次来到异世界、曾是少年的他成为了溺爱的年长骑士
高等學校世代,我從學塾體育場館看過一本科普書,對於逝世進程的形容良民影象透闢——
蒼白直溜:一般說來時有發生於死去後15到120分鐘。
屍斑:殍較低部位的血液沒頂。
屍冷:閉眼以後超低溫的退。常溫一般說來會安樂驟降,直到與情況溫度一模一樣。
屍僵:死人的四肢變得幹梆梆,不便走或搖動。
我和發小的地下戀情
腐爛:屍分化爲概括形式物質的歷程,伴隨着火爆嗅的脾胃。
忘性優質吧。
突,有道光穿透暗噸糧田底。我看到一條非常規的車行道,四圍是瑾的骨料,像魔女區的得天獨厚,又像古舊的地宮。燈光下有個小雄性,穿上打襯布的勢單力薄行頭,流觀賽淚與泗,趴在弱的親孃隨身老淚橫流,幹的女婿冰冷地抽着煙——二話沒說叮噹清朗的讀書聲,他也化爲了一具屍首,後腦的洞眼冒着熟食,膏血浸流了一地,沒過小男孩的腳板。有裡年女人牽着男性,走進一條謐靜的街道,宣傳牌上縹緲寫着“睡覺路”。這是棟年青的房,異性住在地窖的軒背後,每篇陰雨天昂首看着松香水涌動的馬路,人們炯或邋遢的雨鞋,間或還有女裙襬裡的隱私。男性目擔心,尚無笑顏,臉蒼白得像幽魂,只兩頰煞白,朝氣時越來越駭人聽聞。有天深宵,他站在地下室的窗邊,街當面的大內人,叮噹慘的尖叫聲,有個男性跳出來,坐到洞口的墀上抽噎……
永別了,遺失品 漫畫
我也想哭。
但我單單一具異物,不會潸然淚下,只會流膿。
很快我將成爲炮灰,躺在杉木或鉻鎳鋼的小起火中,酣然於三尺之下的黃土奧。或許,橫在魔女區道路以目陰冷的網上,高低潰爛成一團髒乎乎的物資,連耗子與臭蟲都無意來吃,末被微生物吞噬乾淨,直到成一具少壯的骨頭架子。
如果有格調……我想我名特優去人,親眼覽氣絕身亡的要好,也能張下毒手我的刺客,還能蓄水會爲上下一心報復——成爲撒旦,烈性的怨念,暫時水印在魔女區,乃至五代普高周遭數千米內。
死後的宇宙,大校是未嘗時日望的,我想此怨念會是世世代代的吧。
動畫網
而人在,就不成能恆久,不過死了。
人從一物化千帆競發,不饒爲着等待閉眼嗎?左不過,我伺機得太瞬間了少許。
或許,爾等中會有一期智多星,在異日的之一黎明或夏夜,獲悉誣陷我的鬼胎底細,而且挑動殺害我的殺人犯。
誰殺了我?
淌若再有來生?如果還有來生?苟還能雙重來一遍?如若還能避免盡錯處和疵瑕?好吧,教育決策者疾言厲色,雖我剛殺了你,但只要在另一個小圈子相逢你,我抑或想跟你說一聲“對不住”!
如同睡了由來已久的一覺,肌體恢復了神志,僅僅係數人變得很輕,幾乎一陣官能吹走,私心莫名興奮——這是復活的行狀?
小說
情不自禁地站起來,去魔女區,刻下的路卻那麼生分,再度從來不破舊的瓦舍,倒更像舊書繡像裡的畫面。渺茫失措地走了青山常在,時是一條昏天黑地的羊腸小道,兩邊是繁榮的密林,土壤裡隱約現枯骨,還有月夜裡的粼粼鬼火。頭頂響着貓頭鷹的哀嚎,時常有長着顏面的鳥雀飛過,就連身子都是太太的造型,是否傳聞中的姑獲鳥?
酋長的背叛之妻 動漫
有條河阻遏我的去路,拋物面竟自恐怖的血色,滿腥味的熱風從濱襲來,捲曲的波濤黑乎乎藏着人影與發,怕是剛溺死過好幾船人。順川走了幾步,涓滴沒感觸膽怯,才挖掘一座古老的石拱橋。青色的石欄杆上邊,坐着個灰白的老奶奶,僂着體不知有點歲了,讓我溯兩天前才凋謝的外婆。她端着一個破瓷碗,盛滿熱氣騰騰的湯水。她昂首看着我的臉,髒亂差吃不消的眼神裡,裸某種迥殊的大驚小怪,又略惘然地搖動頭,鬧慘焦枯的音:“爭是你?”
野良神櫻花
老太婆把碗塞到我前面,我厭地看着那層湯海上的油膩:“這是何等者?”
“喝了這碗湯,過了這座橋,你就能居家了。”
因此,我信而有徵地拿起碗,抑制和好喝了上來。鼻息還不壞,就像外婆給我煮過的豆腐腦羹。
老婦人讓到另一方面,鞭策道:“快點過橋吧,否則趕不及了。”
“趕不及投胎嗎?”
這是我在戰國高中閱時的口頭語。
“是啊,小。”
話說內,我已流經這座古老的小橋,折衷看着橋下的淮,全方位家庭婦女長髮般糾紛的水草。剛踩彼岸漠然如鐵的寸土,就騰陣子莫名的反胃,撐不住地長跪唚始於。
真憐惜,我把那碗湯渾吐出來了。
當我還毋折返神來,一聲不響的大溜已倏忽漲,霎時間將我淹沒到了水底。
在長滿狗牙草上上下下屍骨的暗中坑底,一塊非常規淡漠的光從某處射來,照亮了一番人的臉。
那是屍首的臉,亦然二十五歲的闡發的臉。
而我行將成爲另一個人。
今後我不用人不疑古籍裡說的——人死後都要通過鬼門關,登上陰世路,在達到陰曹之前,還有一條限界的忘川水。通過河上的奈何橋,過這條忘川水,就激切去扭虧增盈轉世了。若何橋邊坐着一番老太婆,她的名字叫孟婆,如若不喝下她碗裡的湯,就過不得若何橋,更渡無盡無休忘川水,但假若喝下這碗孟婆湯,你就會忘前世的通欄追憶。
忘川,孟婆,今生。真正會忘掉一嗎?
“如若還有他日?你想奈何飾你的臉?而付之東流未來?要怎麼說回見?”